20世纪90年代初,浩叔带着他的妻儿回家过年。站在那个给他留下无限酸楚和快乐的破茅草房前,他心里波澜起伏。
他脚下是他曾经和朋友、家人反复踏过的土地,院子里长满了蒲公英和车前草;风雨中飘摇的所谓的房子里,飘出一股呛人的霉味;那仅能容纳一张架子床的房间湿气沉沉,蔓草已爬上床头。城里的妻儿很是惊异,这就是他曾经日夜思念的故乡?
邻居的一声叫喊让他回到现实:浩呢,回来了?浩叔回答道:是的,回来了。他趁着这股劲向邻居借了锄头铁铲,把院子里的杂草给锄了,顺便捡了一些干草烧水擦桌子,擦门板。
一番打扫后,他坐在院子里思绪起伏,和孩子讲起了曾经的往事。浩叔高高大大,白皙的皮肤,无论谁看见都会称他为美男子。生于斯长于斯,他也热爱家乡。但家里太贫穷了,有劳力却无处使用。田地稀少,收成靠天。为了摆脱贫苦的现状,他努力读书,希望靠读书闯出一番天地。父亲早逝,母亲借钱让他读书。浩叔没有辜负母亲,一直孜孜不倦,平时成绩很优秀。读到高中,参加高考,无奈造化弄人,高考时生病,他与理想大学失之交臂。现实狠狠地把他打回原形,他继续回到农村。
家里的房子,其实称不上房子,充其量是一个庇护所。兄弟几个和侄子侄女等挤在破旧的茅草房,叹个气打个喷嚏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每天起床,面临的是无米之炊,女眷们起床不是东家借米,就是西家借钱。看着侄儿们面黄肌瘦,兄嫂们为了生存吵闹不止,他满心疲倦,真想离家出去躲躲清静。
他没事就出门走走,与同自己一样高考失意的朋友商量寻找出路。他们认为,和村人一样捕鱼,靠天吃饭,是不可能的,必须找一种能实现自己价值的相对体面的工作。于是,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三人决定创办私立学校。三个高考落榜的大男人在村里借用别人闲置的老宅,打扫干净,收拾一番,搬来自家的桌子凳子,用门板当黑板,叫来自己的侄子侄女及亲戚组建班级,简易的私立学校、农村最早的私立学校就这样成立了。
每天听着孩子们的朗读,看着孩子们写作业,他们仨脸上出现了久违的笑容。他们三人负责三个年级,在他们的指导下,学生成绩很不错:真希望这么和谐美好的生活能长久下去。
村庄经常遭遇洪灾,渔民生活捉襟见肘。村里没有重视读书的风气,小孩刚刚认得几个字就被父母拉下来放牛捕鱼。遇上洪灾,辍学捕鱼的越来越多,村小学的学生越来越少,浩叔的私立学校更是举步维艰,几年后还是逃不了生源流失、学校停办的命运。
靠仅有的五分田无法养活自己,更不用说做房子,娶妻生子,他们便纵有满腹才华,更与何人说。
浩叔被这种艰难的生活激怒了,但又不能沉沦,一定不能沉沦。他曾试着和其他村民一样靠捕鱼缓解捉襟见肘的困难,重复村上古老的故事,但苦于没有帮手,20大几的大龄男青年,因为贫穷,娶不了老婆,照顾不了年迈的母亲,这确实遭同样贫穷的村民嘲笑。要生存,就得找出路。
他兄弟、侄子靠水吃水,用推网捕鱼虾卖给别人,但依然杯水车薪。看见本村身强体壮的男青年砍柴卖柴改善生活,他也试着跟随,然而一次经历彻底击碎了他的梦想。一天傍晚,他到山上劈了两捆杉树枝,打算用来围菜园,却不知那时村委已通知封山育林,杉树枝属于禁砍的范围。在回来的路上,还没有到渡口,就被守山人抓住,罚款。村长敲锣打鼓全村通报,相当于现在的记大过,并罚款五元用来放电影。
浩叔几乎被推到风口浪尖上,成了全村茶余饭后的谈资。人们一边看电影《刘三姐》一边嘲笑他,觉得他就是小偷,并坚定地认为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。过河时,在渡船上遇见浩叔,人们调侃他;路过他家门口,大家指指点点。他成了祥林嫂,村民仿佛是鲁迅笔下的柳妈和无聊的男子。失望孤独一起涌向他,他彻底愤怒了,但无处申辩,也不容申辩,无人听他申辩。
几天后,他走到河边,站在这养活他却又不能培育他不能让他实现理想的河流面前,沉思。他用手撩起清澈的河水,小鱼虾在自由地游戏,水中央不时地有大鱼翻身。
浩叔突发联想,浅水处只有小鱼小虾嬉戏,看起快乐,但很快就会被渔网网住,而深水处的大鱼才能自由,不由得想起自己学过的文章“积土成山,风雨兴焉;积水成渊,蛟龙生焉”。他不能成为浅水区的小鱼虾,一定要成为深水处的蛟龙。
那年,适逢洪水侵蚀,村庄一片荒凉,庄稼歉收。村庄很多刚刚谈好婚事的男子汉因为贫穷被退婚,村上的大龄光棍又增加了不少。
几天后,浩叔收拾自己的心情,和自己做了艰苦的思想斗争,和侄子学生聊了自己的想法,告诫他无论如何都要读书,借钱也好,讨饭也罢,必须读书。他拣了几件衣服,告别母亲,告别侄子,走出村庄,搭上去宁波的列车。破旧的客车发动时发出沉重的闷响,从鄱阳一路向东,一头扎进那苍茫的夜色中,扎进繁华的港口城市宁波。夜色朦胧,脑海里幻化出无数镜头,以往的,未来的。他像一个逃亡者,更像一个身无牵挂的游侠,像一个为爱情而私奔的激进者。
到了宁波,他收过破烂,做过破烂王,卖过菜;没有暂住证,被驱赶过。渐渐地他熟悉了环境,考察市场需求,分析形势,在宁波站稳了脚跟,那曾经令人不屑的破烂王变成了收入颇丰的奋斗者;告别了曾经促狭逼仄的破旧的出租房,住进了城市的敞亮的居民区。夕阳照着他的背影,他感到了以前不曾有过的尊严,体会到城市的温柔。他本能地仰起了脸,享受着上天的眷顾,他在城里踏出的每一行脚印都曾发出铮铮的脆响。后来村里的同龄人纷纷告别妻儿,离开那特别想摆脱又不忍摆脱的村庄,奔向城市。
额头的伤口可以不必隐藏,他带着光驯服生活中的每一头怪兽,想起了以往,想起了自己孤身走暗巷的挣扎,想起了自己与绝望对峙的过程,他流下了热泪。
村上越来越多的人去赌命运的枪,他们背井离乡,前往宁波。他们在贫穷的黑夜中呜咽和怒吼,擦掉摔倒时的污垢,去实现自己最卑微的梦。他们逃离蛮荒,借助改革开放的春风,实现最卑微的梦和最孤高的梦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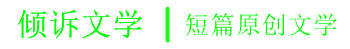
查看所有评论